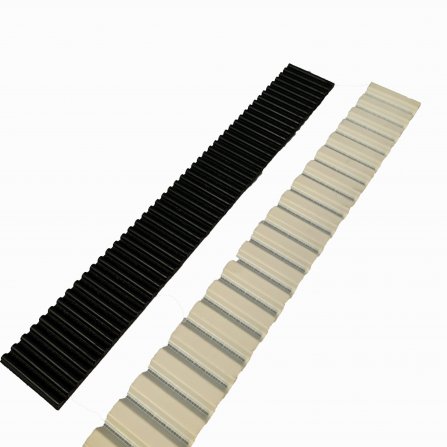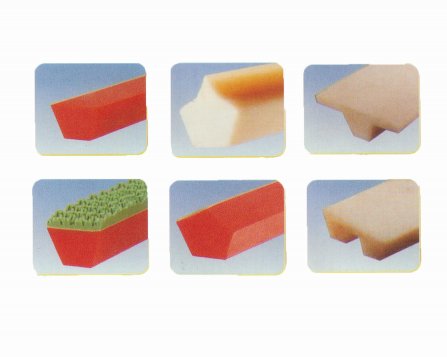印刷(shuā)包裝工(gōng)廠轉型之路:AI數字員工引領增效新潮流
在競爭日益(yì)激烈的印刷包裝行業,傳(chuán)統的運營模式正(zhèng)麵臨諸多挑戰。如何提升效率(lǜ)、降低成本、優化客(kè)戶體驗,成為眾多工廠亟待解決的(de)問題。而AI數字員(yuán)工的出現,為印刷(shuā)包裝工廠開辟了一條全新的增效之路,尤(yóu)其在自助接待和自(zì)動報價演示方麵,展現(xiàn)出巨大的優勢(shì)。一、傳統困境:效率低下與客戶流失風險在過去,印刷包裝工廠的(de)接待